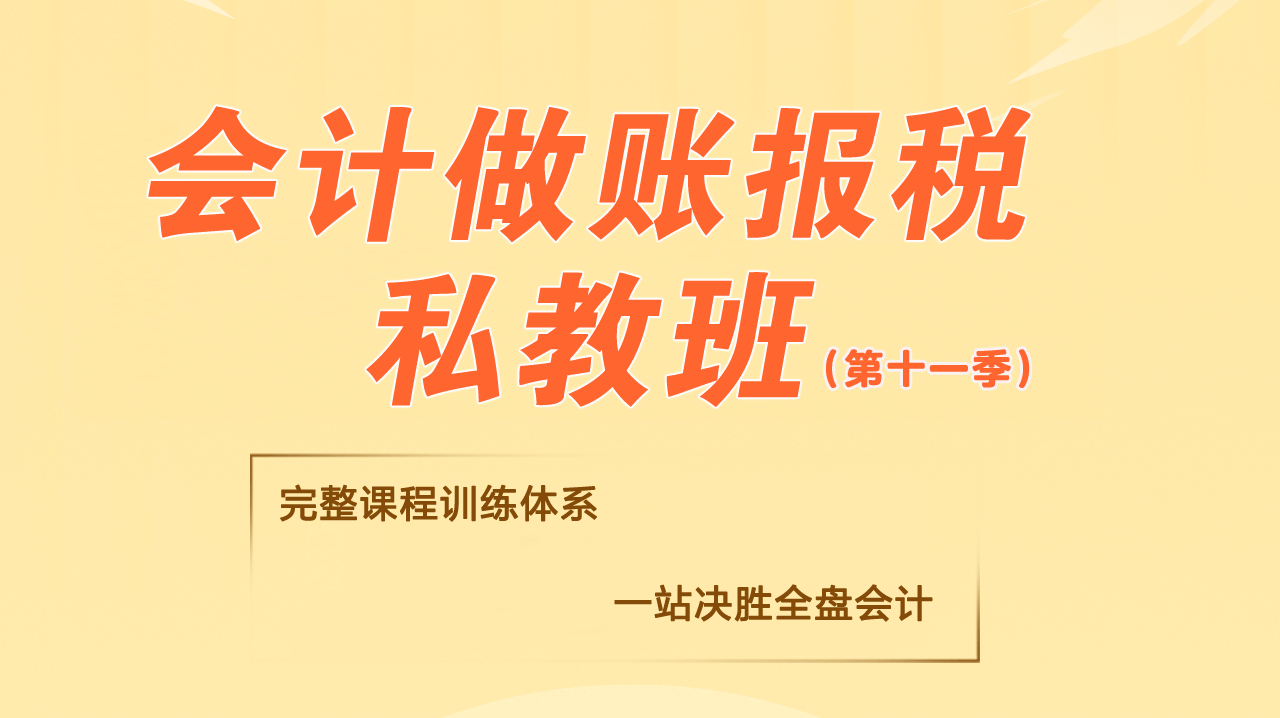中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来源: 马蔡琛
2004-02-05
普通
当前,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已逐步过渡到以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利用政府预算总括反映政府财政收支的特性,实现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的预期目标。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借鉴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总结与梳理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与发展方向,对于正确把握今后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演进模式
目前关于建国以来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论述,大都集中讨论有关财政体制的变迁问题。这诚然是预算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预算管理制度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如前所述,预算管理制度不仅包括预算体系内处理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主要是各级政府间财力分配关系)的预算管理体制,(注:通常论述中,狭义的财政管理体制就是预算管理体制,而广义的财政管理体制还包括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等。在此,我们采用狭义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还包括预算原则、组织形式、预算范围的变化趋势和预算工作程序等管理和制度层面的问题。而分级财政体制的变迁涉及的更多属于政府间财力分配的问题,它虽然最终合成为决定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既有预算管理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如果仅以财政体制的变迁为标志划分我国预算管理制度的演变阶段,就会产生一些错觉,认为财政体制发生了变化预算管理制度也将同步变化。实际上,在财政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由于预算管理人员受到既有路径依赖的影响,只要原预算管理制度能够继续维持,我们总是尽可能维持原有制度框架。直到财政体制变迁导致的利益分配格局重组,使得原有制度难以为继时,才会发生预算管理制度的变迁与创新。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尝试重新划分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根据制度变迁的有关经济理论加以分析。
建国50年来,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预算管理制度的产生阶段(1949年—1951年)
新中国的国家预算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建立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各革命根据地曾编制过财政预算,但那只属于战时财政预算。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根据地被分割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统一的国家预算。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着手编制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1949年12月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1950年财政收支概算编制的报告》,这标志着新中国国家预算的诞生。1951年8月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基础上,政务院又发布了《预算决算暂行条例》,我国的国家预算管理制度从此建立起来。
2.长期相对稳定阶段(1951年—1992年)
这是一个跨度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间财政体制大体经历了统收统支、总额分成、分级包干等多个历史阶段。基本的变动趋势是,从50年代的高度集中型,到70年代以集中为主,适度下放财权的类型,到80年代的地方分权为主,放权让利的类型。但其间预算管理制度则保持总体相对稳定,其特点表现为:在预算形式上采用单一预算,预算编制原则上贯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原则,长期沿用基数法编制预算,预算编制程序上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上下结合,逐级汇总的方法,预算管理总体上比较粗放,预算编制透明度不高等。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关系长期处于不断变化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彼此的利益分割的多重博奕问题上,缺乏通过优化预算管理内部制度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激励机制,从而导致预算管理制度变迁长期滞后。
3.中央政府供给主导型阶段(1992年—1998年)
以1992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为标志,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进入以权力中心提供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主要框架的供给主导型阶段。《条例》规定,我国国家预算采用复式预算编制方法,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从1992年起,中央预算按复式预算形式编制。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又进一步明确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划分为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三部分,待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增设其他预算。从1995年开始,地方预算也按复式预算编制。(注:根据笔者的了解,目前我国大部分地方政府预算并没有按复式预算编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着缺陷。)
关于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长期滞后于财政体制变迁的原因(滞后期约10年),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体制的多变性,导致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缺少较为稳定的政策框架,中央和地方政府只有在财政体制相对稳定时,才有可能推进预算管理制度的变迁。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偏重于政府支出安排的预算管理制度,属于财政改革深层次的问题,必须首先经历财政收入领域的率先改革,才有可能加以进行,这也是符合我国财政改革的历史趋势与逻辑结构的。三是预算管理制度的变迁,更多的涉及政府内部公共管理的范畴,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的开始,只有等待权力中心率先提供制度供给才有可能进行。地方政府的各级预算管理人员受到原有路径以来的影响,也难以率先突破既有的管理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时期内,部分地方政府试行了零基预算改革。安徽省(1994年起)、河南省(1994年起)、湖北省(1993年起):云南省(1995年起)、深圳市(1995年起)等省市结合自身的财政预算现状,借鉴国外经验,突破了传统的采用“基数法”编制预算的框架,实行了零基预算改革。这使得这一时期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具有了某些“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萌芽。
4.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并存的阶段(1999年至今)
以1999年初河北省正式启动“预算管理改革方案”和同年9月财政部提出改变预算编制办法试编部门预算为标志,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进入了“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并存阶段。
1998年8月,河北省制定了《改革预算管理推进依法理财的实施意见》,并于1999年3月按新模式编制了2000年省级预算。
1999年9月,财政部在《关于改进2000年中央预算编制的意见》中指出,2000年选择部分部门作为编制部门预算的试点单位,细化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草案的内容。
与此同时,天津、陕西、安徽等省市也相继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了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创新。天津市在借鉴市场经济国家预算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于1999年实行了标准周期预算管理制度;陕西省率先在全国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安徽省从1999年起在全省实施了综合财政预算。这一系列改革举措表明,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方式已经进入“中间扩散型”(注:我国学者杨瑞龙(1998)提出的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通过考察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特殊作用,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作出了以下推断: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步向中间扩散型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与“供给主导型”并存的阶段。
二、今后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
(一)“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长期并存
在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之所以会存在“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长期并存的局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预算管理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其制度变迁机制与其他领域有所不同
按照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理论,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必须经过权力中心的事后追认。当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需求与权利中心的初始制度供给意愿不一致时,地方政府总是设法突破在给定的体制条件下权力中心设置的进入壁垒。
但是,在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多级预算体制,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预算,立法审批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就预算程序而言,与世界各国没有大的区别。对于下级人大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批,上级人大原则上不加以干预,预算执行中合规合法性的审查,也主要由其本级人大负责。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本年预算执行情况和来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也无须上报上级政府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因此,地方政府关于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行为,无须经过上级政府的追认。其成功经验其他地方可以直接借鉴,从而横向构成“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权力中心也可以纵向借鉴地方政府的创新经验,或用于本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实践,或纵向建议其他地方政府参考借鉴。这是当前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两种模式同时并存的法律基础。
2.率先进行“中间扩散型”制度创新的地方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老工业基地
在“阶梯式的制度变迁模型”中,由地方政府推进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一般率先发生在发达地区。因为地方政府若想进行自主的制度创新,既要事先认识到进一步改革的好处,又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但是,在始于1999年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率先进行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地区,大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老工业基地。这些地区财政收入规模有限,而发展本地区经济对财政资金的需求却更为迫切。在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规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前提下,只有通过预算管理制度上的创新,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才能满足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现状使得“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创新方式长期并存的局面成为了现实的可行选择。
就率先创新的地方政府而言,消极等待权力中心提供新的预算管理制度创新供给,则无法及时摆脱资金紧张、捉襟见肘的局面。同时,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供给是针对普遍地区而言的,而本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制度供给短期内难以缓解自身资金紧张的局面。在比较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后,这些地方政府具有了成为制度创新中“第一行动集团”的内在冲动。因此,今后一定时期,“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还将在预算管理领域长期存在。并且,在经济起飞阶段,即使是经济较发达地区也会感到财政资金紧张的压力,那些率先进行预算管理制度创新地区的成功经验,也会促使经济较发达地区加以效仿,“中间扩散型”制度创新方式的范围还会不断扩大。
就权力中心而言,由于预算管理改革属于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对此必须慎重,加之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当前,如果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进行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创新,对于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大国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只有既承认并鼓励地方政府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创新行动,并择其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又要针对各地普遍情况,适时提供制度供给,保持全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方向总体一致性。
(二)随着制度变迁中新的“第一行动集团”的成熟,逐步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模式转化
在现阶段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角色的主要是权利中心(也可认为是中央政府)或是各级地方政府。但是,政府预算是政府财政收支活动的集中反映,公共财政的职责就是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在公众面前的具体反映就是政府公共预算。现代预算管理的核心就是通过对公共资金的筹集和配置,来影响和保持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
追溯现代预算制度的起源,我们会发现,其基本理论构架是:国家与公民之间构建一种社会契约。在这种社会契约中,国家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尤其是产权保护,而公民则向国家纳税,国家是由纳税人养活的。作为国家财政资金的提供者——公民,自然有权全面了解政府是如何花费公民自己的钱的。其监督国家对公共资金使用情况的主要工具就是政府预算。因此,如果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着问题,通过改进预算管理制度获取潜在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大于克服既有路径依赖的边际成本时,公民就会推动自身的代言人——最高国家权利机关(如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与政府财政部门进行集体博奕,公民本身则作为第二行动集团,协助“第一行动集团”完成预算管理领域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
现阶段,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主要是由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作为“第一行动集团”发起进行的。他们作为既有预算管理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受到既有路径依赖的影响,所进行的预算管理制度创新往往难以尽如人意。同时,个别地方的财政预算部门从自身部门利益出发,往往设法掩盖预算资金分配中的具体博奕过程;这就使得作为预算管理法定监督者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公众更难于完全打开预算管理的“黑箱”。
今后,随着广大公众预算管理知识的普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管理过程介入程度的不断深化,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方式最终将向“需求诱致型”模式转化。但这种转变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仍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1998,(1):3-10.
[2]杨瑞龙,杨其静。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式[J].经济研究,2000,(1):24-31.
[3]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项怀诚。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项怀诚。1999中国财政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丛树海。中国预算体制重构——理论分析与制度设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7]麦履康等。中国政府预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8]杨之刚。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一、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演进模式
目前关于建国以来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论述,大都集中讨论有关财政体制的变迁问题。这诚然是预算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预算管理制度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如前所述,预算管理制度不仅包括预算体系内处理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主要是各级政府间财力分配关系)的预算管理体制,(注:通常论述中,狭义的财政管理体制就是预算管理体制,而广义的财政管理体制还包括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等。在此,我们采用狭义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还包括预算原则、组织形式、预算范围的变化趋势和预算工作程序等管理和制度层面的问题。而分级财政体制的变迁涉及的更多属于政府间财力分配的问题,它虽然最终合成为决定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既有预算管理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如果仅以财政体制的变迁为标志划分我国预算管理制度的演变阶段,就会产生一些错觉,认为财政体制发生了变化预算管理制度也将同步变化。实际上,在财政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由于预算管理人员受到既有路径依赖的影响,只要原预算管理制度能够继续维持,我们总是尽可能维持原有制度框架。直到财政体制变迁导致的利益分配格局重组,使得原有制度难以为继时,才会发生预算管理制度的变迁与创新。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尝试重新划分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根据制度变迁的有关经济理论加以分析。
建国50年来,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预算管理制度的产生阶段(1949年—1951年)
新中国的国家预算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建立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各革命根据地曾编制过财政预算,但那只属于战时财政预算。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根据地被分割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统一的国家预算。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着手编制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1949年12月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1950年财政收支概算编制的报告》,这标志着新中国国家预算的诞生。1951年8月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基础上,政务院又发布了《预算决算暂行条例》,我国的国家预算管理制度从此建立起来。
2.长期相对稳定阶段(1951年—1992年)
这是一个跨度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间财政体制大体经历了统收统支、总额分成、分级包干等多个历史阶段。基本的变动趋势是,从50年代的高度集中型,到70年代以集中为主,适度下放财权的类型,到80年代的地方分权为主,放权让利的类型。但其间预算管理制度则保持总体相对稳定,其特点表现为:在预算形式上采用单一预算,预算编制原则上贯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原则,长期沿用基数法编制预算,预算编制程序上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上下结合,逐级汇总的方法,预算管理总体上比较粗放,预算编制透明度不高等。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关系长期处于不断变化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彼此的利益分割的多重博奕问题上,缺乏通过优化预算管理内部制度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激励机制,从而导致预算管理制度变迁长期滞后。
3.中央政府供给主导型阶段(1992年—1998年)
以1992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为标志,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进入以权力中心提供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主要框架的供给主导型阶段。《条例》规定,我国国家预算采用复式预算编制方法,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从1992年起,中央预算按复式预算形式编制。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又进一步明确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划分为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三部分,待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增设其他预算。从1995年开始,地方预算也按复式预算编制。(注:根据笔者的了解,目前我国大部分地方政府预算并没有按复式预算编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着缺陷。)
关于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长期滞后于财政体制变迁的原因(滞后期约10年),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体制的多变性,导致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缺少较为稳定的政策框架,中央和地方政府只有在财政体制相对稳定时,才有可能推进预算管理制度的变迁。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偏重于政府支出安排的预算管理制度,属于财政改革深层次的问题,必须首先经历财政收入领域的率先改革,才有可能加以进行,这也是符合我国财政改革的历史趋势与逻辑结构的。三是预算管理制度的变迁,更多的涉及政府内部公共管理的范畴,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的开始,只有等待权力中心率先提供制度供给才有可能进行。地方政府的各级预算管理人员受到原有路径以来的影响,也难以率先突破既有的管理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时期内,部分地方政府试行了零基预算改革。安徽省(1994年起)、河南省(1994年起)、湖北省(1993年起):云南省(1995年起)、深圳市(1995年起)等省市结合自身的财政预算现状,借鉴国外经验,突破了传统的采用“基数法”编制预算的框架,实行了零基预算改革。这使得这一时期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具有了某些“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萌芽。
4.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并存的阶段(1999年至今)
以1999年初河北省正式启动“预算管理改革方案”和同年9月财政部提出改变预算编制办法试编部门预算为标志,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进入了“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并存阶段。
1998年8月,河北省制定了《改革预算管理推进依法理财的实施意见》,并于1999年3月按新模式编制了2000年省级预算。
1999年9月,财政部在《关于改进2000年中央预算编制的意见》中指出,2000年选择部分部门作为编制部门预算的试点单位,细化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草案的内容。
与此同时,天津、陕西、安徽等省市也相继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了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创新。天津市在借鉴市场经济国家预算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于1999年实行了标准周期预算管理制度;陕西省率先在全国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安徽省从1999年起在全省实施了综合财政预算。这一系列改革举措表明,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方式已经进入“中间扩散型”(注:我国学者杨瑞龙(1998)提出的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通过考察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特殊作用,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作出了以下推断: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步向中间扩散型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与“供给主导型”并存的阶段。
二、今后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
(一)“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长期并存
在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之所以会存在“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长期并存的局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预算管理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其制度变迁机制与其他领域有所不同
按照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理论,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必须经过权力中心的事后追认。当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需求与权利中心的初始制度供给意愿不一致时,地方政府总是设法突破在给定的体制条件下权力中心设置的进入壁垒。
但是,在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多级预算体制,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预算,立法审批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就预算程序而言,与世界各国没有大的区别。对于下级人大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批,上级人大原则上不加以干预,预算执行中合规合法性的审查,也主要由其本级人大负责。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本年预算执行情况和来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也无须上报上级政府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因此,地方政府关于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行为,无须经过上级政府的追认。其成功经验其他地方可以直接借鉴,从而横向构成“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权力中心也可以纵向借鉴地方政府的创新经验,或用于本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实践,或纵向建议其他地方政府参考借鉴。这是当前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两种模式同时并存的法律基础。
2.率先进行“中间扩散型”制度创新的地方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老工业基地
在“阶梯式的制度变迁模型”中,由地方政府推进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一般率先发生在发达地区。因为地方政府若想进行自主的制度创新,既要事先认识到进一步改革的好处,又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但是,在始于1999年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率先进行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地区,大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老工业基地。这些地区财政收入规模有限,而发展本地区经济对财政资金的需求却更为迫切。在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规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前提下,只有通过预算管理制度上的创新,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才能满足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现状使得“中间扩散型”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创新方式长期并存的局面成为了现实的可行选择。
就率先创新的地方政府而言,消极等待权力中心提供新的预算管理制度创新供给,则无法及时摆脱资金紧张、捉襟见肘的局面。同时,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供给是针对普遍地区而言的,而本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制度供给短期内难以缓解自身资金紧张的局面。在比较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后,这些地方政府具有了成为制度创新中“第一行动集团”的内在冲动。因此,今后一定时期,“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还将在预算管理领域长期存在。并且,在经济起飞阶段,即使是经济较发达地区也会感到财政资金紧张的压力,那些率先进行预算管理制度创新地区的成功经验,也会促使经济较发达地区加以效仿,“中间扩散型”制度创新方式的范围还会不断扩大。
就权力中心而言,由于预算管理改革属于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对此必须慎重,加之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当前,如果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进行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创新,对于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大国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只有既承认并鼓励地方政府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创新行动,并择其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又要针对各地普遍情况,适时提供制度供给,保持全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方向总体一致性。
(二)随着制度变迁中新的“第一行动集团”的成熟,逐步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模式转化
在现阶段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角色的主要是权利中心(也可认为是中央政府)或是各级地方政府。但是,政府预算是政府财政收支活动的集中反映,公共财政的职责就是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在公众面前的具体反映就是政府公共预算。现代预算管理的核心就是通过对公共资金的筹集和配置,来影响和保持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
追溯现代预算制度的起源,我们会发现,其基本理论构架是:国家与公民之间构建一种社会契约。在这种社会契约中,国家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尤其是产权保护,而公民则向国家纳税,国家是由纳税人养活的。作为国家财政资金的提供者——公民,自然有权全面了解政府是如何花费公民自己的钱的。其监督国家对公共资金使用情况的主要工具就是政府预算。因此,如果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着问题,通过改进预算管理制度获取潜在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大于克服既有路径依赖的边际成本时,公民就会推动自身的代言人——最高国家权利机关(如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与政府财政部门进行集体博奕,公民本身则作为第二行动集团,协助“第一行动集团”完成预算管理领域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
现阶段,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主要是由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作为“第一行动集团”发起进行的。他们作为既有预算管理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受到既有路径依赖的影响,所进行的预算管理制度创新往往难以尽如人意。同时,个别地方的财政预算部门从自身部门利益出发,往往设法掩盖预算资金分配中的具体博奕过程;这就使得作为预算管理法定监督者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公众更难于完全打开预算管理的“黑箱”。
今后,随着广大公众预算管理知识的普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管理过程介入程度的不断深化,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变迁方式最终将向“需求诱致型”模式转化。但这种转变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仍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1998,(1):3-10.
[2]杨瑞龙,杨其静。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式[J].经济研究,2000,(1):24-31.
[3]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项怀诚。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项怀诚。1999中国财政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丛树海。中国预算体制重构——理论分析与制度设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7]麦履康等。中国政府预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8]杨之刚。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