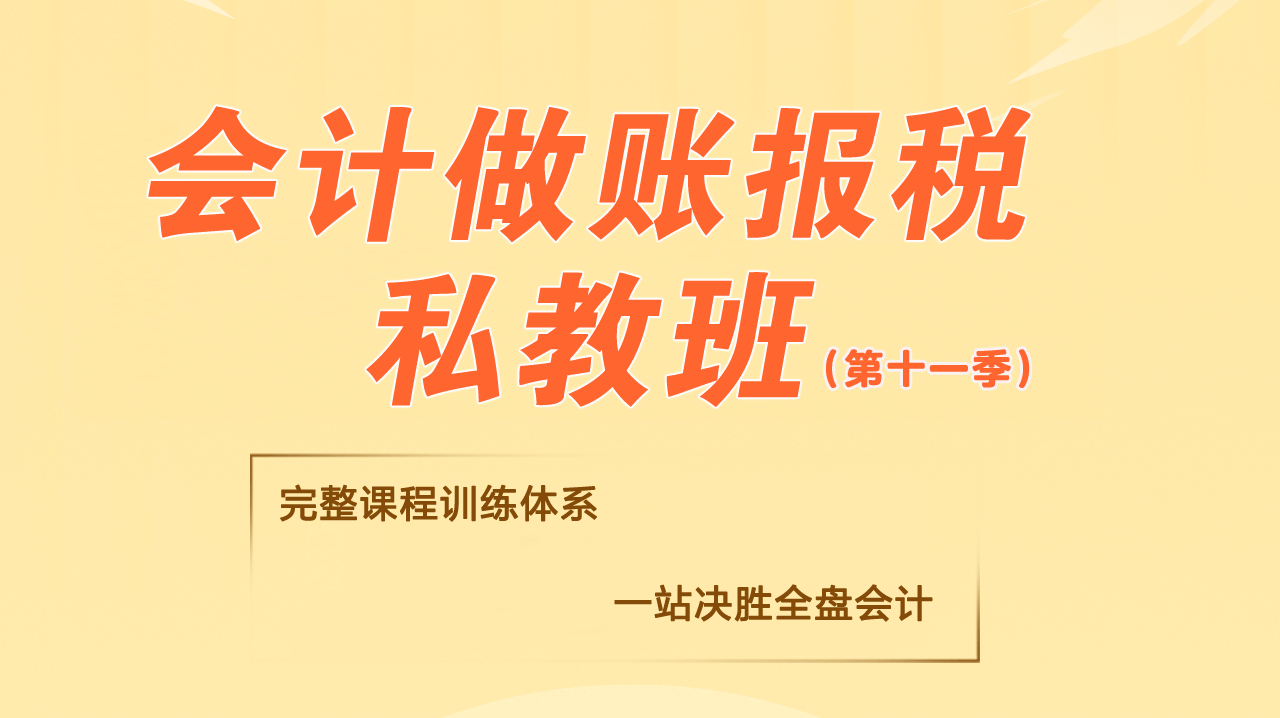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
摘要:经济增长一向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而税收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就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税收及税种结构、税负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进行分析和述评,对于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经济增长;税收;税种结构;税负结构
经济增长一向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以往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从财政理论层面上说明如何制定和调整税收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或是分析税收收入与GDP二者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及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但对税收这个经济变量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数量关系,税收及税收结构是通过哪些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适合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和财政体制要求的最优税收结构是什么样的研究则很少。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对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述评。
一、税收的经济增长作用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政府的税收政策和经济增长很久以来就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联系在一起。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Adam Smith(1776)的《国富论》。Smith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一国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生产工人与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劳动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劳动分工,而产生分工的必要条件则是资本积累,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以上分析,Smith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来实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由于资本积累依赖于投资,而投资的动机来源于预期利润的驱动,征税会降低预期利润,影响资本积累;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税收都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所以,税收不应该设定得过高,设定税负水平的原则应该是能低则低;同时,国家的职能应尽量减少,政府的最佳角色是充当经济生活的“守夜人”,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经济。
David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和税收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他认为社会一切收入都应该征税,税收不是来自于资本,就是来自于收入,都是对积累的减少,因而从总体上看,税收不利于经济增长,并且来自于资本的税收比来自于收入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更大。因此,Richado对于税收的思想与Smith是一脉相承的,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少征税。Thomas Malthus(1802)认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因素:资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节约劳动的新发明,随着经济的增长,为了使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保持足够的有效需求。而由国家税收维持的政府非生产性消费是保持产品与消费平衡的重要因素,所以征税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Malthus不赞成Smith和Richado的观点,他主张增税,不赞成减税,他认为要把征税带给私有财产的损失,与征税带来有效需求的增加从而维持和刺激生产增长的好处加以比较,主张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牺牲前者,换取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促进财富的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始于Ramsey(1928)的经典论文。Ramsey首次采用变分法来分析消费者跨期最优选择问题,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和增长问题的基础,为进一步探究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方式提供了数量分析工具,开创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Keynes(1936)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理论,颠覆了传统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有效需求决定供给水平,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运行。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Keynes认为,税收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合适的税收政策取决于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首先应该减税并扩大政府支出,以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次应该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促使有效需求的提高,最终使得宏观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在凯恩斯学派税收调节理论的基础上,Paul Samuelson(1948)发现,当实行超额累进所得税制时,税负水平会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自行进行调整,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动稳定的功能,发挥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与此相应,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形势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经济发展,这时税收可以被视为经济的“人为稳定器”。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Harrod(1939)和Domar(1946)以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的思想方法,把短期静态均衡推广应用到经济的长期动态过程来建立经济增长理论,在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采用生产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完全不可替代的Leon-tief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用以分析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实际上取决于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但由于采用资本一劳动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均衡很难达到,得到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被称为是“刀锋上的均衡增长”。Solow(1956)和Swan(1956)对Harrod和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形式进行了修正,采用新古典形式的C-D生产函数,在资本和劳动可以平滑替代的基础上,研究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虽然Solow-Swan模型对经济现实的模拟更进了一步,但结论与Harrod-Domar模型基本一致,对产生经济增长的机制的描述是相同的,即经济增长的源泉仍然来自于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为了使经济系统实现长期的人均增长,Solow又对原有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技术进步变量A,并允许技术持续进步,但是技术变量仍然是外生的,以固定比例g增长。沿着平衡增长路径,经济增长由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不变技术进步率来决定。Harrod-Doma模型和Solow-Swan模型为人们洞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然而模型的一个明显缺陷是,长期增长完全由外生的因素所决定。Solow是第一个检验税收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人,但Solow的结论是税收政策并不能影响增长率;也就是说,虽然长期来说征税确实降低了产出水平,但不管税收政策如何对经济造成扭曲,都不会影响长期增长率。 在Solow研究成果的基础上,Mankiw、Romer和WEil(1992)发现,在生产函数中考虑人力资本后So- low模型拟合得更好,但引入人力资本并未改变模型的基本结论。虽然没有改变经济外生增长的基本结论,但他们强调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认为技术进步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这种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机械化的。20世纪60年代,Cass(1965)和Koopmans(1965)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但储蓄率的内生性也并没有消除长期人均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由于储蓄率是内生的,那么在模型中引入税收因素将改变储蓄的回报,从而影响到消费者储蓄和投资的决策,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长。在Cass-Koopmans模型中引入资本所得税以后发现,征税使得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储蓄率降低,稳态产出水平下降。但是当经济达到稳态之后,人均产出将不再发生变化,即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经济增长率完全由技术进步决定,而与税率无关;也就是说,在短期内,税率的提高确实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是在长期内,税收政策只有水平效应,却没有增长效应,税率的提高对平衡增长率没有任何影响。这一结果使得税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因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对税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税收的福利效应、税率变化的短期增长效应及其对稳态资本劳动比的影响。
由于这段时期的增长理论中所采用的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的,因此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这些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增长的机制是外生的,因此,这段时期的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外生增长理论。正因为增长的机制是外生的,这种外生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和机制,而且外生增长的机制使得政策因素游离于增长之外,政府不能通过采取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体现在税收上就是这段时期的税收思想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收制度的设计不能扭曲个人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外生增长理论中税收并不能影响增长,直到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才为研究税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行的分析工具。
(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贝克尔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
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现状,人们采取逐一放松外生增长模型假设前提的方式,通过将储蓄率、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等重要外生变量逐步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从而克服了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关键性质,构造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内生于模型,长期增长是在模型之内而非被一些诸如未加解释的技术进步之类的外生增长变量所决定,这就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简明地模拟了增长的产生过程,并且通过对增长过程的模拟,描述了模型暗含的税收对个人决策的影响。内生增长模型提供了一个解释和理解历史数据的视角,并给出了未来政策变化的结果,这一点对于理解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重要,通过这些模型,我们可以理解和预测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实现内生增长,需要采取由经济中参与人的选择所决定的某种方式来克服边际产出递减。从现有文献来看共有四种方式可以实现,所有这些方式都通过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同样的目的——经济持续增长。
最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是AK模型,假定资本是唯一的投入,规模报酬不变,产出由函数Y=AK给出。在AK模型中,长期增长率由正的固定的资本边际收益决定,那么对资本所得征税将直接降低资本的边际收益,因而征税会直接影响长期增长率。
第二种方式是引入人力资本,并假定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要素的增长同步。人力资本的存在会放松对于广义资本而言的报酬递减约束,从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能导致长期人均增长。模型中有两个投资过程: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如果从广义上把资本视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那么就可以克服要素边际报酬递减,使经济内在产生增长。这样的模型既可以是单部门的,也可以是两部门的。Barro、Mankiw和Sala-i-Martin(1992)构建了单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生产技术相同,生产函数均采用不变规模报酬的C-D形式。从更广义的角度讲,单部门模型就是AK模型的延伸,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的增加都将提高产出和消费的增长率。在税收效应上结论与AK模型相同,即对物质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征税都将直接降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从而直接降低了长期增长率。Uzawa(1965)和Lucas(1988)构建了两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生产技术不同,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不平衡程度。此时,税收不仅影响物质资本积累,还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并且对物质资本征税和对人力资本征税对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由征税所带来的税收扭曲,尤其是税收结构扭曲将持久影响经济增长率。
第三个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方法是企业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干中学”。Ro-met(1986)借用了Arrow(1962)的框架,在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的“观念”具有非竞争性和外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干中学”模型,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一是假设“干中学”要靠每个企业的投资来获得,而且一个企业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同样增加;二是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知识一经发现就立刻外溢到整个经济范围内,从而使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都得到提高。与Solow的结论不同,Romer认为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对增长可以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
第四个选择是,可以假定产出依赖于劳动和其他要素的投入,在不摒弃任何其他传统的投入要素的情况下,技术以新的投入要素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Romer,1987和1990;Barm,1990),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各种不同的政府活动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可被视为一种其他投入要素,政府性活动的变化等价于对技术水平A的修正,从而等价于生产函数的移动,影响在朝向稳态的转移过程中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在这方面主要是以生产性公共品提供为切入点来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相应的政策空间,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引入使得经济在竞争企业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实现内生增长。在公共支出模型中,税收对增长率的影响是交错的,一方面税收会减少私人部门的税后边际产品并降低增长率,另一方面税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公共支出的供给,进而提高私人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增长率,这与之前的各种模型的研究结果完全不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税率的提高对增长没有任何影响。在人力资本模型中,即使税率对增长率产生影响,税率的提高一般只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不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
二、税种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关于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内外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两点,一是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确实有着 重要的影响,二是不同的税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同,有的税种与增长率负相关,有的税种与增长率正相关。
Engen Eric和Skinne Jonathan(1996)的研究表明,在外生增长模型中,当税收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在沿着可能较长的转移路径向新的稳态转移过程中,短期产出增长率会相应做出调整;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税收可以通过税收结构和税率的调整来影响产出增长率,而且,税收的组合(即税收结构)与税收的绝对水平对经济增长来说同样重要,通过采用税基较宽的税收结构并加强有效管理来整合税收资源的国家,可以比征税水平普遍较低且无效率的国家有较高的增长率。Se-Jik Kim(1998)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一般税收体系主要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估计了美国税收收入中性(税收收入全部用于财政支出)条件下,税收结构的变化对增长率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他认为一国的税收对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影响,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税收结构的不同是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增长率差异的大约30%;二是偏好的不同可以解释增长率差异的大约4%,其余约70%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技术的不同;三是劳动所得税、证券债务率和通货膨胀也是解释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他还发现在个人税收安排上,劳动所得税造成国家间增长率显著不同的作用,同资本所得税同样重要,而且发现每个税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严格依赖于税收体系本身,并且在相应的税收体系中,税收收入中性的变化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增长效应,在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中约有超过30%为总税收水平内部的变化所引起的。总的来说,在税收收入中性的情况下,税收结构有着巨大的增长效应。
Kneller、Bleaney和Gemmell(1999)选取22个OECD国家1970~199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税收结构和政府花费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非扭曲性税收和生产性政府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Gareth Myles(2000)在相对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从内生增长的视角估计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结论是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而税收结构可能比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更重要。Zagler、Martin和Dtlmecker、Georg(2003)认为,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宽泛和显著。消费税仅仅扭曲劳动和休闲之间的选择,由所得税向消费税的转移将鼓励资本积累,当然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所得税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消极的,会抑制经济增长。通过对税收结构的研究,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扩张的需要,开始调整税收结构,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从以直接税为主向以税基比较宽泛的间接税为主转移。
对发展中国家税收结构的研究不是很多,其中,Burgess和Stem(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结构可以随时间进行调整以最大化增长率;同时他们还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税率与单位资本GNP之间存在微弱的但却显著的关系,而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显著的关系。Lehmussaari(1990)的研究也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税收结构和税收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Zee(1996)则分别对24个OECD国家与56个非OECD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税收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除了工业化国家和非洲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增长与征税水平、税收结构和税收的稳定性之间存在比较弱的统计关系。
国内对税收结构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直接税和间接税水平的层面上,主要结论是:一是直接税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不利于经济增长,间接税与经济增长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二是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关系不协调;三是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应该尽量减少直接税而主要采用间接税。
马栓友(2001)认为,目前的直接税/间接税比率均已超过其最优数量比率,应适当削减直接税。范广军(2004)利用我国1981~1998年数据,采用OLS方法估计了我国财政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就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直接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间接税的符号为正但不显著异于零,增加我国的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提高间接税收占GDP的比重则不影响经济增长。中国社科院“增进城市经济竞争力的环境税制研究”课题组(2004)认为,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不协调,直接税所占比重过低,间接税十分不完善,这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不协调的原因,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认为,我国目前直接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税收总额的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税制结构不够合理,税种设置不够科学。
国内对税种结构进行分类研究的很少。王亮(2004)采用1992~2002年税收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变化轨迹,结论是流转税和所得税都与经济增长呈现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得到使我国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的流转税、所得税占GDP的比率分别为7.78%和2.1%,但我国目前流转税的实际占比偏高,税改重点应为降低流转税的比率,同时增大所得税比率的结论。李绍荣、耿莹(2005)从税收结构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和要素产出效率的影响出发,说明了在中国现行税收结构中各种税类的份额对经济增长和要素收入分配的效应,并指出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结构调整方向。他们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收结构下,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单纯地从税收结构的数量调整上讲,目前应提高所得税类的税收份额,并降低财产税类的税收份额。苑小丰(2009)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就中国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税负的增加对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但降低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流转税类份额的增加提高劳动的产出效率,降低资本的产出效率;所得税类份额增加提高资本产出效率,降低劳动产出效率。同时,所得税类份额的增加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流转税类份额的增加则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说明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有必要加强税收体制改革,适当调整所得税类份额,促进生产模式转变,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三、税负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负担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税收理论问题,又是我们进行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选择的核心问题,也是能否实现公平分配、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
(一)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外文献的观点是,一般来说,短期内税收负担水平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长期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Chamley(1986)和Judd(1985)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动态最优税制,分析表明,长期来说,对资本所得征税的最优税率为零。Milesi-Ferretti和Roubini(1998)把这个结论扩展到了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并且除了分析劳动和资本所得税收以外,还用来分析消费税。他们发现对劳动所得和消费征税的长期最优税率也为零。
对不随时间变化的税率的分析比较有限,结果相对一致。Cooley和Hansen(1992)的研究表明,税率随时间变化的税收政策相对于税率不随时间变化的税收政策而言,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要小。Comez(2007)采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计算了美国经济的最优固定比率税收结构,发现短期内资本所得的最优税率相对于参数的变化极其稳定,而工资税和消费税之间的平衡却显著依赖于投资于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商品的税收待遇,并在较轻程度上依赖于跨期替代弹性。
Roy W.Bahl和Richard M.Bird(2008)通过对经济发展和税收政策设计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末,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税率为33.4%,约为发展中国家的2倍;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率基本没变,一直保持在17%左右;而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转型经济的宏观税率略微有所下降,为21.8%,税收负担水平无论是与收入水平还是经济增长率之间都没有必然的联系。Gareth Myles(2000)在相对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从内生增长的视角估计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结论表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Tanzi(2000)则指出大多数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税率与经济增长无关。
关于税率的短期影响,Engen Erie和Skinner Jonathan(1996)在对美国税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后认为,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Se-Jik Kim(1998)的实证结果是,资本收益税将平均对增长率带来2%的影响,个人所得税将解释增长率不同的20%。而更多的结论是资本所得税比劳动所得税的作用大,但Kim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对两国增长率不同的影响上至少与资本所得税同样重要。Mendo-za、Razin和Tesar(1994)的研究也表明,当税率变动1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相应变动大约0.25个百分点。
但以下研究成果则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Georgios Karras(1999)运用11个真实增长率和税率显著不同的OECD国家1960~1992年的数据,分别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了税率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一是与平滑税收假设理论相一致,虽然税率表现为显著持续的改变,但产出增长率则没有这个特点;二是较高的税率会永久减少产出水平,但对产出增长率却没有永久的影响。这些发现同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不一致。而Joel Slemrod等(2003)则认为高税率并不必然降低经济增长,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高税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二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实际上用在了更能提升经济增长的方面。Christos Koulovafianos和Leonard J.Mimlan(2004)在内生增长框架下研究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如果没有产出的外部性,边际税率会减少资本积累的回报率。因此,在不存在生产的外部性的框架下,边际税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率总是导致竞争经济偏离产出的有效性和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边际所得税率的降低并不必然外生地带来经济的大幅增长。
Burgess和Stem(1993)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税率与单位资本GNP之间存在微弱的但却显著的关系,但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显著的关系。
具体到我国的情况,由于对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认识不一致,理论界对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宋效中等(2005)以巴罗的模型为基础,利用我国1985~2004年小口径宏观税负的统计数据,在考虑公共支出的情况下,对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我国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不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宏观税负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降低0.14个百分点。李永友(2004)把财政支出纳入到了税收负担分析的框架内,通过对我国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税收负担即使在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对经济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程度在两种情况下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不考虑政府支出时,税收负担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713个百分点;但在考虑财政支出之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由原来的0.713个百分点下降到0.33个百分点左右。刘军(2006)通过运用1978~2004年的中国经济数据建立模型,计算得到我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税收负担每上升(下降)1%,经济增长率下降(上升)3.866%;并且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也有影响,但影响度比较小,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每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
(二)税收负担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国外税收制度与我国的税收制度相去甚远,这里仅综述我国的研究情况。武利华(2000)认为在我国区域税收负担结构中,西部税负最重,东部次之,中部最轻,并指出自1985年两步“利改税”以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各地区税负差异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申嫦娥(2006)通过采用汉森一萨缪尔森模型,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说明了当前区域税负主要受人均GDP、城市化程度、产业结构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改变目前区域税负差异的途径在于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削弱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李永友、丛树海(2005)利用跨省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1994—2002年地区税负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税收负担在我国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但与大多数观点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东部地区税负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地区税负最低,其中最高的东部地区比最低的中部地区在1994~2002年之间平均高出近7个百分点,并且这一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而且他们还对区域内税负差异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平差异进行了研究,认为就平均税负而言,东部地区各个体之间的税负差异最大,但这种差异程度有下降的趋势,不过下降的幅度不是非常明显;中部地区个体间的差异程度最小,但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这种差异程度在逐步上升;从整体上看,不同地区内的差异程度在不同区域间有趋同的趋势。此外,河南省税务学会课题组(2007)也认为在区域税负差异中,东部税负较重,西部税负次之、中部最轻。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张文春等(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