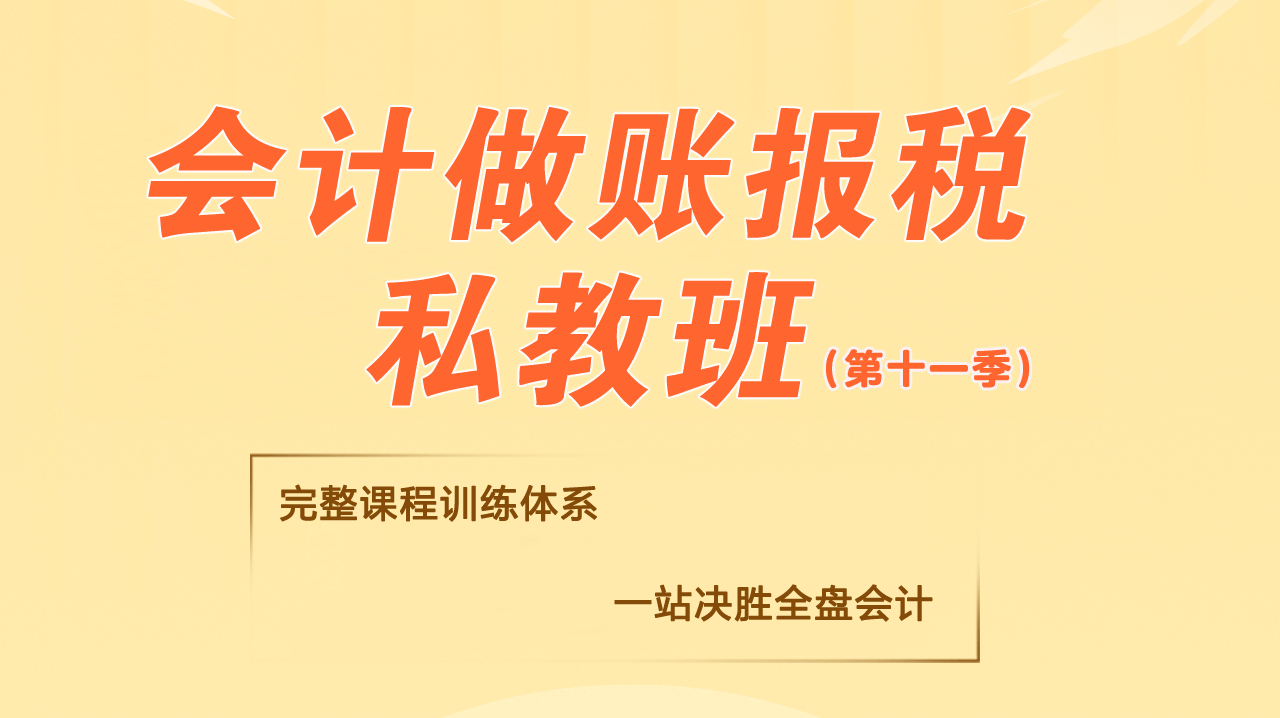分税制的完善在于财权与事权的统一
1994年分税制实施之后,我国以极快的速度确立了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走出了中央和地方就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不断讨价还价的困境,传统的财政包干体制被废止,初步规范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进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并一直保持至今。可以说,1994年的分税制较好地调整了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收入与支出的关系,但对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却未作出明确规定。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收入划分由省政府自行决定,这就在制度上留下了一个缺口。在利益驱动下,分税制造成的收入上收的效应就难免在各级政府间层层传递,省级政府的财力集中程度不断增大,从1994年到2000年的6年时间中,由16.8%上升到22.4%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市级政府也在效仿,财政收入占到36.5%.2000年地方财政收支相抵,净结余105亿元,而县、乡财政赤字增加。到2004年,省级财政收入占25.9%.地(市)占36 6%,两者相加占62.5%,。说明实际上财力是在向省、市级集中。
在财权越来越集中的同时。政府的基本事权却在下移。地方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1993年为78%,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即迅速下降,仅为44.3%,此后的十年间一直在这个水平徘徊。而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变化很小甚至增大,1990年为68%左右,2004年则微升至75%左右。
可以看出,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央集中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约占财政总收入的50%~60%左右,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划分几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即分税制没有改变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格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责,带有非常强的外溢性特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理应由中央政府提供,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依此来确定。如果由财力严重匮乏的基层政府来承担,必然会导致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或严重不均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背离,分税制就无法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的作用,更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源缩减,促使其从预算外寻找收入来源。城市财政主要以出卖土地为自己筹集财政收入,越是东部地区。卖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越高,据周天勇先生的估计,2006年,全国各地的土地出让金加起来有7000亿元左右,大部分没有进入预算。而县乡财政则只能靠收费和罚款来维持。由此,一种新的“二元财政”的格局开始形成。这是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新变化。越是在农村,越是在农业地区。越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越是基层的小集镇和小城镇,对个体、中小企业的收费、罚款就越严重,甚至让路政、交管、城管等上路收费和罚款,搜刮过路的汽车司机。2006年,地方政府各部门所收的预算外收费和罚款估计高达12000亿元左右。而越是这样做,县乡经济就越是萧条,投资少、创业难、就业机会少,甚至失去了吸收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出现了近年来剩余劳动力过度向大中城市转移和流动的现象。财政部有关人士向《凤凰周刊》透露,地方各级政府积累的显性和隐性债务,目前已达到4000多亿元。
有一种说法,认为分税制确实把超过半数的财政收入集中到了中央政府的手里,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钱都被中央政府自己花了,实际上,其中60%到70%的钱是由地方政府支出的。地方政府的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约40%,其支出却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60%到70%,中间的差额是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解决的。
问题在于,现行转移支付存在着体制缺陷,转移支付到了县乡这一级政府很难做到透明、规范。转移支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专项补助进行的,至于补给谁、不补给谁,补助量的多少,既缺乏严格明确的规定,也不是严格依据事权而定;既没有公开的预算,也不受人大的监督检查,完全由官员个人负责操作,这就难以避免拨款的随意性,也极容易造成县乡财政收入的不稳定、不公正。
应当明确,基层财政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分税制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于分税制不到位。只有完全、彻底的分税制才是我国财税改革的科学与理想的模式。理顺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的事权和财权关系,至少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由中央负责的事(职责)就全部收归中央,应该由地方负责的事(职责)就全部下放地方,真正做到各行其是,各负其责。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谈过,笔者则强调它的法治性,即在科学划分之后,要由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成为国家的一项法律,不管是哪一级政府,决不能“越界”。
第二,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再根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应按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来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范围,国防、外交等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中央财政负责;跨地区大型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兼有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共产品特征的事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并按具体项目确定分担的比例;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等中央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更为有效的事项,应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把相应的财力给予地方来完成:其他属于区域内部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则由地方财政负责,相应的财权、财力应全部划归地方。
第三,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税种。中央与地方都应拥有只属于自己的主体税种、税收征收管理权、完善的税收征管体系,以及相应的充足的税源和财力。为做到这一点,可考虑适当提高共享税中的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如从25%提高至30%),而酝酿中的不动产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新税种,都应该划为地方税种。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各级政府都有相应的财权和财力保证,实现该中央办的事由中央财政承担、该地方办的事由地方财政承担的目标。这些虽是老生常谈,却不得不一谈再谈,因为这是实行分税制最应该具备的先决条件。
完善分税制的最为关键之点是“一个降低、一个规范”。
一是降低财权的集中度。中央应果断放权,坚定不移地走“分权”之路,将税收管理权包括税收立法权、解释权、税基税率选择确定权、税种开征停征权、减免权、调整权等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合理划分,不应全部集中在中央。中央税与共享税的立法权、征收权、管理权可集中在中央:对于不在全国统一开征、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地方税的立法权、解释权、征管权可全部划给地方;对于全国统一开征、对宏观经济有较大影响的地方税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可由中央制定基本法规和征收办法,相应给予地方一定的征管权、税率确定权和政策调整权等。 二是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充分考虑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的人、自然环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教育卫生与市政建设、特殊性等因素,细致测算各地的标准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建立起地方各级政府的标准预算。中央财政分配应倾向于不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在拨款比例、专门项目、各种补贴等方面,实行特殊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人均收入越低,人均建设转移支付也就应越多,即“吃饭钱”要大体相同,达不到基本标准就应该实施重点转移支付。笔者建议,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应介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和监督过程。如有必要,可考虑制定“转移支付法”。应当向社会公开资金的分配办法、资金规模、申请条件、资金分配去向、使用结果和效果。一定规模以上的项目,应纳入发展计划和预算,须经人大审核,并接受人大监督。各部委专项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也必须随时接受人大和新闻舆论的质询和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与事权体制,既是经济体制问题,也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涉及中央和地方在动员、支配经济资源上的权责划分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集权与分权关系依据何种原则处理。而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一件关系“全局稳定”的大事,采取的是慎之又慎的态度,但现在至少有一件事不可再拖:改革政府行政体制,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这不仅是政府运行的高效、便利的问题,更是由于它关系到分税制的未来。
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在同一个政治体制框架下,构建一个分布于广大区域的、条件差异显著的、多级政府层次的财政体制,难度何其大也。怎样把20多个税种在五级半政府之间按分税制要求切分?如何确定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支出结构?且不说欠发达地区,即使是在发达区域,省以下的四级如何分税?数得着的大的税种已经全部共享,省以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则五花八门,有的安排了复杂易变的分享办法,有的则干脆实行包干制,各级政府间“扯皮”、“讨价还价”的现象更是难于消除,而这都不是分税制体制下应该出现的情形。地方基层财政困难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五级财政框架与分税分级财政逐渐到位之间的不相适应性日渐突出所致。
“十一五”规划要求“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减少行政层级”上面,“着力”建设中央、省、市(县)三级行政架构,即乡镇政权组织变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地级能不设的不设,如需设立则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使事权的划分清晰化、合理化。这样就可以使省以下的分税制由原来五级架构下的“无解”,变为三级架构下的柳暗花明,构建起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级财税体制,再配之以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必能有效地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形成一种可保“长治久安”的财政管理体制。